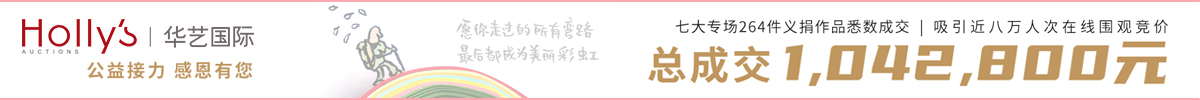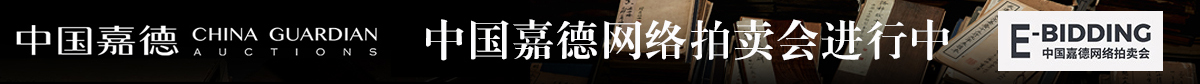与朋友聊天都说长沙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活动是越来越多了,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从前长沙的艺术就像在潜水,自己背着氧气瓶呼吸,现在通过展览和活动,大口大口地喘气,与周围作交换了。看看我们工作室的一面墙,满满都是“湖南千年时间”的展览海报,三年时间,30多场次。
从办展的经历来说,这么多场次下来,“湖南千年时间”团队早已是轻车熟路,每每与朋友谈到“湖南千年时间”的展览时,还是会收到种种的建议,甚至批评。不是我们不努力,也不是我们做得不好,而是大家对“湖南千年时间”有了太多的寄望,有了太多的期待。
有观点说:艺术一但挂到艺术馆的墙上,艺术就死去了。艺术是在创造、被认知、被否定、再创造中不断推进。艺术馆的职能也在不断地发展:展示、推广、艺术市场、甚至参与艺术创作。长沙的艺术馆太少,我们怎么做都是好的,当我们展示曾经的艺术时,来吧,大家来看艺术的“尸体”,反正从前看得也少;当我们展示当下的艺术时,来吧,大家来看我们如何推动艺术潮流。
都说“湖南千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”是一个非常漂亮艺术空间。这曾是“湖南千年时间”的骄傲,但随着对艺术展览的探索发展,空间又成为了“湖南千年时间”的禁锢,如果只在这个空间,“湖南千年时间”所畅想的本土艺术氛围,鼓励的艺术创作思维,倡导的生活艺术风尚都是有局限的。在2012年初,我们用“微展览”打破艺术馆空间,从形式、空间、交互渠道上进行了创新,是非常有益的尝试,“湖南千年时间”向前走了一步。
2012年4月的某个晚上,当文鹏一份“非现场”的草案与几瓶啤酒一起摆到桌子上时,我们都是很兴奋的。“非现场”不是展览,没有一个完整的展览形态,不需要空间,没有展览的仪式,我们称之为“非现场当代艺术项目”。如果说“微展览”是展览形式、展览渠
道的一种创新,“非现场”更是将创新延伸到艺术的创作与呈现过程中来了,对“非现场”的艺术全程进行记录,压缩、解压缩,是将数字时代的特征融入到艺术创作与呈现过程中,并将创作与呈现融为一体了,因此文鹏提出“数码美术馆”的概念来。
“一个人”,“一件作品”,“一个月”,“任何地方”,“不限体裁”…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关键词,让“非现场”变得神秘而有激情。有人问什么是“非现场”?我不知道回答,因为“非现场”是开放的,只有在它实实在在发生之后,我也才知道。但是,我知道“非现场”不是什么。
“非现场”不是展示艺术的“尸体”,因为“非现场”最终展示的很可能不是一件独立架上艺术品。我们将看到的不仅只是一个结果,更是一个过程,艺术思维的过程,艺术创作的过程,我们更关注这个过程,可能是图片,可能是影像,也可能还有其他。而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,没有结果又何妨呢。
“非现场”不是行为艺术。“一个月”容易让人联想起谢德庆的“一年”,“非现场”不是以身体为媒介的艺术,在“非现场”的最终呈现时,创作者也会对创作的思维与过程进行解读,这个解读的过程仍然是这个作品的构成部分,这样“非现场”的介质和性质与行为艺术是完全不同的。
“非现场”不是文献展。可能我们会看到文字资料、图片、影像等,但大家在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,恰恰是作品解压缩的一个过程,我们看到的不是曾经,不是历史,正是现在发生。那么说,“非现场”的主场在哪里?在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地,也在最后呈现的地方,艺术馆的墙壁就此蒸发了。
“湖南千年时间”是幸运的,有这么多充满创作激情的艺术家朋友,从30多个展览到“微展览”再到“非现场”,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了,“非现场”,我们又走出了一步。